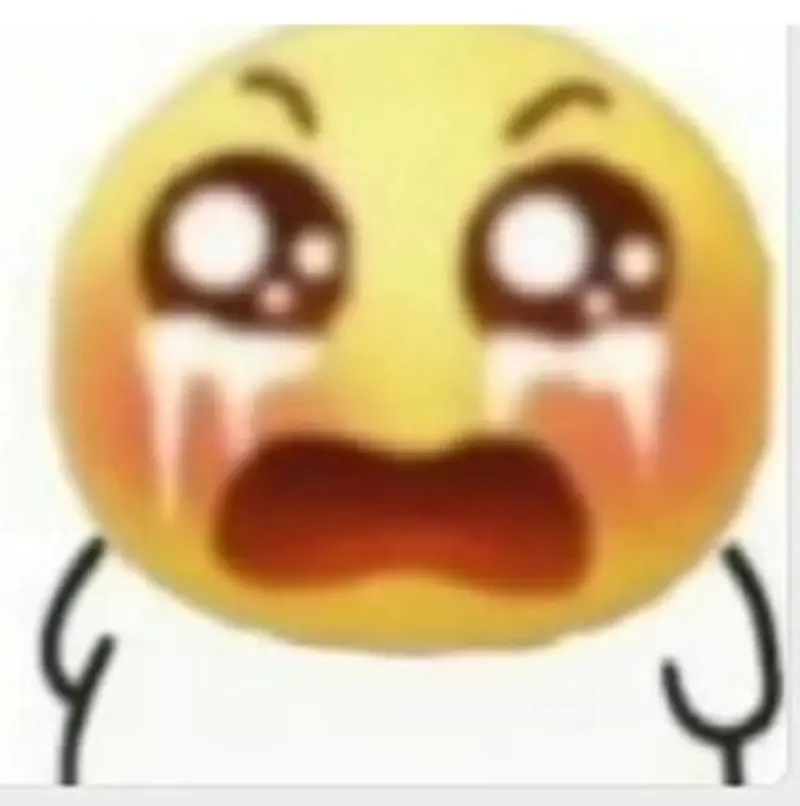何为真实?
这确实是一个大问题。
绝对光滑的圆,统万物于无形的场,人不患不均的共和国,付诸一生的正义...
何为真实?
确切的实体的对“我”的感受,心之所向虚渺的彼岸,具体的经历与“真实人”的交通...
好像对我来说,唯一可以确定只有concept,一个概念,一个看似最抽象,但于我却最真实。
祖冲之永远无法穷尽π的真值,爱因斯坦永远无法统一宇宙场,斯大林永远无法撑起理想的红色国度,摩西永远不能让以色列坚定十诫的正义。那意味着不存在圆,场,共产,正义吗?
非也!非也!非也!
也许我们一生于这泥泞丑陋苟且之尘世勉强过活,即使看透这愚昧无尽头的几十年,我们可能真的只是缸中脑借矩阵母体构想出所谓“真实”的过去,现在,将来,痴痴地自我欺瞒,那海的那边还是海吗?
我无法确定,我无法断言,我是否名为楚门,我是否有希望见到失落的一百年的历史正文,我是否能窥见世界的回放...应该永远不可能...何为真实?连“自己”的确切都存疑,所谓历史又是谁的纪传体?不知道,不可能知道...
“理性总是告诫我,凡是不能完全加以确定的东西,凡是能够找到怀疑之处的东西,我都应小心翼翼地避免相信,就像 避免相信那些显然虚妄的东西一样。”笛卡尔论证到。那么真理是什么?你所看到的一切线索的总和永远小于真相,那我们有什么理由相信我们可以探求真相?这不过是真相的影子,而我们只能先相信这真相才让证据与你的相信所符合,你称其为合理的论证,事实如此吗?在预设的有色眼镜中窥探最后的真理,难道真理与现象的偏差可以忽略吗?
通常我们显得过于理所应当,拒绝思考形而上学,沉溺于形而下学。对理所应当的物之理的近乎疯狂的崇拜,盲目执着于世界是简单的,一贯的,可了解的加速主义中。诚然普罗米修斯的火种借科学之光明,人们走出热带雨林,西装革履,机器轰鸣,这只是亿亿次文明交出唯一的正确答案吗?我不知道...
还好,还好,我有机会去想想这无意义的空虚的“大问题”,concept是真实的。
用尽稿纸也转不出完美的圆,但欧几里得还是创造浩瀚的欧式几何;做尽天马行空的开创也无法统一宇宙各场,但爱因斯坦还是构想出跳脱时间的世界;红色的巨人无法继续前进,但斯大林还是还是给人类提供了一个不关乎地缘血缘只在乎信仰的理想之国;迦南地的奢淫让以色列忘记了耶和华的正义,但摩西还是让这十诫流传至今。我心里有最圆满的圆,有包络万物的场,有理想的乌托邦,有绝对的正义,它们实在地存在,无关乎我的存在,无关乎世界的存在,无关法则的存在。它无须是具体的映射,无须被赋予确切的意义,无须甚至在表象的世界存在过。
笼中鸟不会唱自由之歌,但狱中人是思考的芦苇。躯体困于表象,意识带风筝飞离地球,突破银河眼的禁飞塔。后来的某天,我们收到了云天明的回信,“你好,新人类...”

何为真实?
这确实是一个大问题。
绝对光滑的圆,统万物于无形的场,人不患不均的共和国,付诸一生的正义...
何为真实?
确切的实体的对“我”的感受,心之所向虚渺的彼岸,具体的经历与“真实人”的交通...
好像对我来说,唯一可以确定只有concept,一个概念,一个看似最抽象,但于我却最真实。
祖冲之永远无法穷尽π的真值,爱因斯坦永远无法统一宇宙场,斯大林永远无法撑起理想的红色国度,摩西永远不能让以色列坚定十诫的正义。那意味着不存在圆,场,共产,正义吗?
非也!非也!非也!
也许我们一生于这泥泞丑陋苟且之尘世勉强过活,即使看透这愚昧无尽头的几十年,我们可能真的只是缸中脑借矩阵母体构想出所谓“真实”的过去,现在,将来,痴痴地自我欺瞒,那海的那边还是海吗?
我无法确定,我无法断言,我是否名为楚门,我是否有希望见到失落的一百年的历史正文,我是否能窥见世界的回放...应该永远不可能...何为真实?连“自己”的确切都存疑,所谓历史又是谁的纪传体?不知道,不可能知道...
“理性总是告诫我,凡是不能完全加以确定的东西,凡是能够找到怀疑之处的东西,我都应小心翼翼地避免相信,就像 避免相信那些显然虚妄的东西一样。”笛卡尔论证到。那么真理是什么?你所看到的一切线索的总和永远小于真相,那我们有什么理由相信我们可以探求真相?这不过是真相的影子,而我们只能先相信这真相才让证据与你的相信所符合,你称其为合理的论证,事实如此吗?在预设的有色眼镜中窥探最后的真理,难道真理与现象的偏差可以忽略吗?
通常我们显得过于理所应当,拒绝思考形而上学,沉溺于形而下学。对理所应当的物之理的近乎疯狂的崇拜,盲目执着于世界是简单的,一贯的,可了解的加速主义中。诚然普罗米修斯的火种借科学之光明,人们走出热带雨林,西装革履,机器轰鸣,这只是亿亿次文明交出唯一的正确答案吗?我不知道...
还好,还好,我有机会去想想这无意义的空虚的“大问题”,concept是真实的。
用尽稿纸也转不出完美的圆,但欧几里得还是创造浩瀚的欧式几何;做尽天马行空的开创也无法统一宇宙各场,但爱因斯坦还是构想出跳脱时间的世界;红色的巨人无法继续前进,但斯大林还是还是给人类提供了一个不关乎地缘血缘只在乎信仰的理想之国;迦南地的奢淫让以色列忘记了耶和华的正义,但摩西还是让这十诫流传至今。我心里有最圆满的圆,有包络万物的场,有理想的乌托邦,有绝对的正义,它们实在地存在,无关乎我的存在,无关乎世界的存在,无关法则的存在。它无须是具体的映射,无须被赋予确切的意义,无须甚至在表象的世界存在过。
笼中鸟不会唱自由之歌,但狱中人是思考的芦苇。躯体困于表象,意识带风筝飞离地球,突破银河眼的禁飞塔。后来的某天,我们收到了云天明的回信,“你好,新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