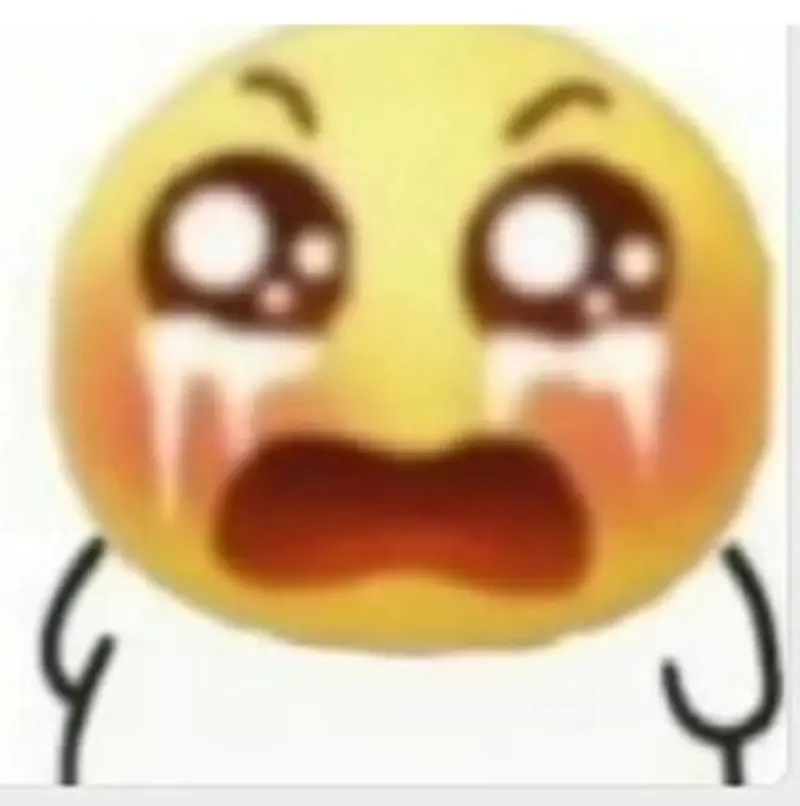从小我就羡慕城里的小孩,因为他们的“喜欢”和我的“喜欢”有些不一样——他们的喜欢叫拥有,而我的喜欢叫克制。
我记得刚上小学的时候,班里很多同学都在传阅小人书,彼时内向的我不敢开口管同学借,就偷偷地问我的母亲,希望她给我买一本,但是母亲一口回绝了我,她反问我道,把我从乡下带到城里读书是为了让我看小人书的么?她没有骂我不懂事,但却让我在自省中沉沦了更久。直到后来有一次大检查,校领导没收了班里所有的小人书,全班唯独我没有,因此获得了校领导的表扬,他们称我为“楷模”,既讽刺又荒诞。
不久后的一个周末,我和母亲去菜市买菜,街口有个小贩在卖书,新的旧的彩图的黑白的铺了一地,母亲低头看了我一眼,抬手示意让我挑一本,我愣住了,直到她第二次抬手,我才兴奋的爬在地上挑了起来。
说来也好笑,我只记得同学们看的书叫什么子,黑白的,好像还有个光头。最后我挑了一本有些旧的《父与子》,但它的作者不叫王泽,而是卜劳恩。母亲拿起来翻了翻,又帮我换了一本更新的《父与子》,为此还多花了五角钱。这本《父与子》没有太多荒诞的幽默,我没像别的同学那样笑得人仰马翻,反倒对早出晚归的父亲多了些话。
小时候我并不喜欢春游和秋游,因为它让我直观的洞悉到了人与人之间的参差。在我只有五元钱筹备整趟活动的时候,别的同学已经拿着百元大钞去玩碰碰车了。我记得那年去青秀山,其他同学在游乐场玩,我自己跑到山腰用作业本写生,画了泰园路口的象和山顶的塔,画两幅画的时间跟他们花完两张百元大钞的时间差不多。回到学校之后,我端详着自己画的画,最后撕下来扔到了垃圾桶里。
往后的年月里,这种克制成了习惯,命运偶尔会给我一些惊喜,让我这个乡下来的孩子也融入了城市生活。从小学到大学,我从未离开这座城市,身边的朋友换了一茬又一茬,我收起了自卑和敏感,换回了一份又一份独立的自信。只是爱情从未坦诚,披着面纱擦身而过,似是而非。
直到我遇到一位上海的姑娘,她只身飞到南宁,一个拥抱就融化了禁锢我二十年的克制,那一刻,爱意如滔天洪水,所有的喜欢都收到了回应,激荡在每一处人生的留白里。
爱情最伟大的时刻不是成就了什么,而是它释放了最真实的自我,至少有那么一刻,全世界都被我抛在了脑后,它让我拥有了最纯粹的自由。
她说过,万万人的世界里,只是相互喜欢,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还有什么值得遗憾的呢?
从小我就羡慕城里的小孩,因为他们的“喜欢”和我的“喜欢”有些不一样——他们的喜欢叫拥有,而我的喜欢叫克制。
我记得刚上小学的时候,班里很多同学都在传阅小人书,彼时内向的我不敢开口管同学借,就偷偷地问我的母亲,希望她给我买一本,但是母亲一口回绝了我,她反问我道,把我从乡下带到城里读书是为了让我看小人书的么?她没有骂我不懂事,但却让我在自省中沉沦了更久。直到后来有一次大检查,校领导没收了班里所有的小人书,全班唯独我没有,因此获得了校领导的表扬,他们称我为“楷模”,既讽刺又荒诞。
不久后的一个周末,我和母亲去菜市买菜,街口有个小贩在卖书,新的旧的彩图的黑白的铺了一地,母亲低头看了我一眼,抬手示意让我挑一本,我愣住了,直到她第二次抬手,我才兴奋的爬在地上挑了起来。
说来也好笑,我只记得同学们看的书叫什么子,黑白的,好像还有个光头。最后我挑了一本有些旧的《父与子》,但它的作者不叫王泽,而是卜劳恩。母亲拿起来翻了翻,又帮我换了一本更新的《父与子》,为此还多花了五角钱。这本《父与子》没有太多荒诞的幽默,我没像别的同学那样笑得人仰马翻,反倒对早出晚归的父亲多了些话。
小时候我并不喜欢春游和秋游,因为它让我直观的洞悉到了人与人之间的参差。在我只有五元钱筹备整趟活动的时候,别的同学已经拿着百元大钞去玩碰碰车了。我记得那年去青秀山,其他同学在游乐场玩,我自己跑到山腰用作业本写生,画了泰园路口的象和山顶的塔,画两幅画的时间跟他们花完两张百元大钞的时间差不多。回到学校之后,我端详着自己画的画,最后撕下来扔到了垃圾桶里。
往后的年月里,这种克制成了习惯,命运偶尔会给我一些惊喜,让我这个乡下来的孩子也融入了城市生活。从小学到大学,我从未离开这座城市,身边的朋友换了一茬又一茬,我收起了自卑和敏感,换回了一份又一份独立的自信。只是爱情从未坦诚,披着面纱擦身而过,似是而非。
直到我遇到一位上海的姑娘,她只身飞到南宁,一个拥抱就融化了禁锢我二十年的克制,那一刻,爱意如滔天洪水,所有的喜欢都收到了回应,激荡在每一处人生的留白里。
爱情最伟大的时刻不是成就了什么,而是它释放了最真实的自我,至少有那么一刻,全世界都被我抛在了脑后,它让我拥有了最纯粹的自由。
她说过,万万人的世界里,只是相互喜欢,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还有什么值得遗憾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