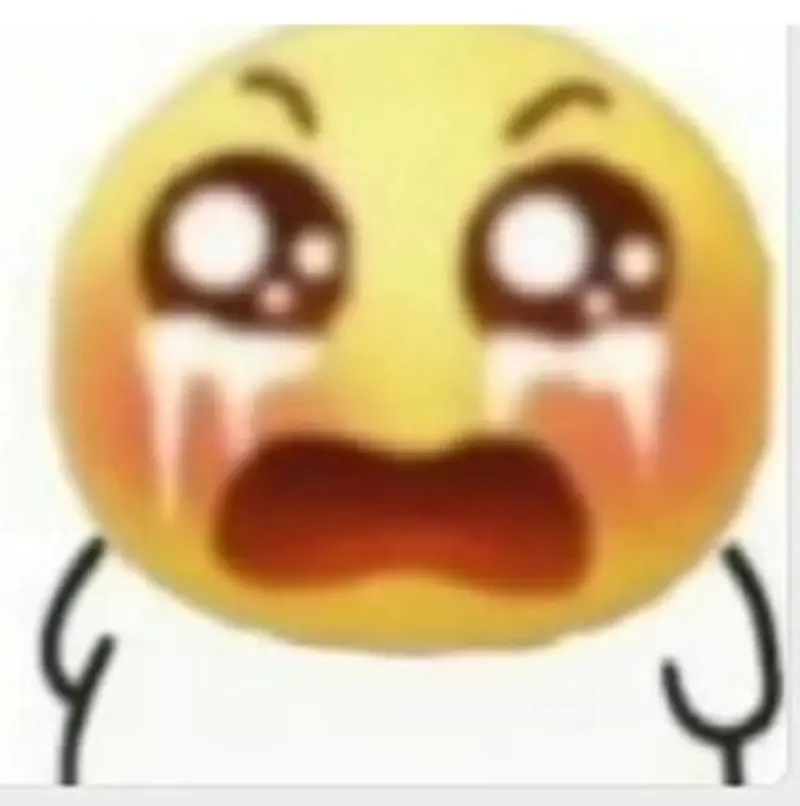TA/Oliver Kay/2024-10-09
克里斯-柯克兰(Chris Kirkland)13 岁时,他的父亲埃迪(Eddie)走进一家投注站,询问他赌自己的儿子能为英格兰国家队出战的话,赔率是多少。
这已经成为博彩公司时常接到的询问之一,但在 1994 年,这并不寻常。他问了几个问题,比如这个男孩是否在职业俱乐部注册。答案是否定的。
博彩公司给出的赔率是1赔100,这促使埃迪下了 98.10 英镑的赌注。这是他和其他家庭成员所能凑到的最大赌注。
当时,柯克兰对他爹的这一奇思妙想一无所知。 他并不看好自己的机会,因为他在当地业余俱乐部巴威尔(Barwell)的 U14 足球队中一直难以获得一场比赛的机会。
三十年后,他在兰开夏郡的家中回忆道:“如果我和父亲一起去博彩公司,他们看到我,我肯定会给他开出比100倍更高的赔率。我当时非常臃肿。我的身材并不是最好的。”
当时,他在前一场比赛中被迫紧急充当门将这一陌生的角色,但表现得很出色。他说:“我的表现肯定没问题。我父亲一定看出了什么。我从将近 14 岁时第一次担任门将,到 18 岁时首次亮相英超联赛(代表考文垂)。这是一个火箭式升级的过程。”

(2000-01赛季,代表考文垂出战英超的柯克兰)
这是非同寻常的。2001 年 8 月,20 岁的他以 600 万英镑的身价加盟利物浦,成为英国最昂贵的门将。22 岁时,他首次获得英格兰国家队征召。当时唯一的意外是,一系列不合时宜的伤病让他不得不等到 25 岁才在与希腊的友谊赛中完成国家队首秀。直到那时,他父亲才终于得到了那笔意外之财。
但他的第一次代表国家队出场也是最后一次,而且由于至今仍不明确的原因,他从未获得过传统的国家队登场纪念帽。直到过去几个月,此事才引起英足总的注意,英足总连忙道歉,并承诺纠正此事。
因此,18 年后的周四,柯克兰将作为英足总的嘉宾,在温布利大球场再次见证英格兰队与希腊队的比赛。43 岁的他终于可以戴上自己的纪念帽了,但他更期待的是他十几岁的女儿露西。

(柯克兰在国家队的唯一一场比赛)
多年来,在柯克兰的成长过程中,他的足球生涯一直在被与折磨和创伤联系在一起——因为这正是足球给柯克兰带来的痛苦,他发现自己陷入了抑郁和止痛药成瘾的泥潭。
2016 年夏天,他在葡萄牙与伯里队一起参加季前训练营时,“服用了大量的药片”,这让他 “发疯”,险些丧命。就在那时,35 岁的他知道自己必须离开足球。是足球正在要了他的命。
直到现在,他才摆脱了毒瘾,重新振作起来。
今年 3 月,利物浦和阿贾克斯之间举行了一场传奇队比赛,为利物浦基金会筹集资金。
除了杰拉德、托雷斯和杜德克等球队传奇人物之外,柯克兰也被征召,这是他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比赛。
他在比赛中只出场了最后 11 分钟,是杜德克和桑德-韦斯特韦尔德之后的第三门将,但这已经足够了。
他说:“我根本不认为自己是利物浦的传奇人物。但当他们问我的时候,我想如果露西能看到我在安菲尔德踢球该有多好。虽然时间很短,但感觉非常棒。我真的没想到我上场时球迷们会这么欢迎我。”

(代表利物浦传奇队出场的柯克兰)
感觉就像回家一样。1988年,利物浦队以5比0大胜诺丁汉森林,这是柯克兰在利物浦的第一场比赛。
只是遗憾的是,他和其他人对自己的利物浦生涯寄予厚望,却从未真正起飞。
这是一笔奇怪的交易。
很少有人质疑利物浦承诺花费高达 600 万英镑购买一名年轻门将的逻辑,因为这名年轻门将在考文垂取代瑞典门将马格努斯-赫德曼后表现出色,被广泛认为是英格兰国门的潜在接班人。
但奇怪的是,利物浦在同一天从费耶诺德签下了波兰国门杜德克。在他下笔之前,接班的计划就已经很明显了——28岁的杜德克负责中短期,20岁的柯克兰负责长期。但在与“令人敬畏”的杜德克进行了一次训练后,柯克兰不知道自己还需要等待多久。

(杜德克和柯克兰是同一天官宣的)
在杜德克状态严重下滑后,柯克兰在默西塞德郡的第二个赛季获得了出场机会,但令人鼓舞的表现却因他在足总杯比赛中与水晶宫前锋德勒-阿德博拉相撞导致右膝后十字韧带断裂而戛然而止。
伤病成了他生存的祸根:手指骨折;在训练中阻挡哈里-科威尔(Harry Kewell)的凶猛射门时手腕骨折;困扰他多年的背伤,最初是在另一次训练中发作,这次是因为蛙跳;2005 年 10 月租借到西布罗姆维奇时,他在与博尔顿流浪者前锋凯文-戴维斯(Kevin Davies)的冲撞中肾脏撕裂。
他说:“我并不是那种肌肉经常受伤的人。那是一连串的意外受伤。”
这些伤病似乎总是在最糟糕的时候发生:他第一次担任利物浦门将出战了 14 场比赛,第二次出战了 11 场比赛,第三次出战了 14 场比赛。2004 年 12 月,在史蒂文-杰拉德(Steven Gerrard)的激励下,利物浦在安菲尔德战胜奥林匹亚科斯,他还在那场著名比赛的板凳席上,但五个月后,当利物浦队在伊斯坦布尔战胜 AC 米兰时,他已无缘欧冠赛场。
后备门将斯科特-卡森(Scott Carson)在赛后为他颁发了冠军奖牌,并指出柯克兰在小组赛中首发出战了四场比赛。但柯克兰拒绝了这块奖牌,他觉得自己没有参与其中。因为背部手术,他无法在贝尼特斯手下看到自己的未来。
离开利物浦后,柯克兰在维冈竞技担任了四个赛季的首发门将,基本上没有受到伤病的困扰,帮助球队留在了英超联赛,并在 2008 年赢得了俱乐部的年度最佳球员奖。他毫不犹豫地将那段时光称为 “我职业生涯中最美好的时光”。

(维冈竞技时期的柯克兰)
2012 年夏天,当柯克兰签约谢周三时,俱乐部坚持在他的合同中加入一项条款,规定如果他因背伤缺席达到一定场次的比赛,俱乐部可以终止与他的合同。
柯克兰确信他的背伤问题已成为过去,但在谢周三英冠联赛揭幕战的前两天,他的背部突然痉挛,这让他陷入了焦虑和恐慌之中,担心所有的老伤病和老毛病都会卷土重来。
过去,当他的背部问题最严重时,医生曾给他开过止痛片曲马多(Tramadol,一种具有成瘾性的止痛药物,被滥用规模最大的精神药品之一)。他感到绝望,于是自作主张,自行用药,宣布自己康复了,并在与德比郡的比赛中再次感觉良好。
但很快,他就发现自己吃药不仅仅是为了治背痛。他这样做是为了缓解从来到谢周三那一刻起就感到的焦虑。
他说:“这是一家伟大的俱乐部——大俱乐部,伟大的球迷——但我的问题是远离家乡。我错过了一切:接女儿放学、看她的校园剧、下午遛狗。我在利物浦和维冈时的日常工作都不复存在了。我还要开车去谢菲尔德——单程只有70英里,但通勤时间太长了,要穿过蛇形山口,高峰时段还要堵在曼彻斯特的路上。”
他说:“我开始在早上 5:45 出发,比其他人早几个小时到达训练场。我真的很焦虑,所以我开始服用更多的药物来缓解焦虑。我的情况越来越糟。曲马多每天最多只能服用 400 毫克。我每天服用 2500 毫克。我把它们装在守门员包里带到球场上。不是因为疼痛,而是因为我上瘾了。我每天醒来第一件事就是吃药,晚上最后一件事也是吃药。”
俱乐部里有人知道他在服用吗?或者他的医生?“不知道,”他说,“我是在网上订购的。没有人知道,甚至利昂娜(柯克兰的妻子)也不知道。”
九个月前,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ADA)将曲马多列入了禁药名单,这意味着如果运动员在赛内检测中对该药物呈阳性反应,将面临长期禁赛的前景。
在过去几年中,有球员私下联系柯克兰,请求帮助他们戒掉止痛药。他说:“我不是说每个球员都这样,但药物成瘾的运动员比你想象的要多。现在止痛药已被列入禁药名单,但如果有人被发现服用止痛药,我也不会感到惊讶。
“它们不会提高成绩。它们不会让你变成超人,也不会让你扑出每一球。它们很危险。这就是问题所在。我曾晕倒、心悸、产生幻觉,病得很重。它们会杀了你,而且它们差点就杀了我。”

(译者注:德转的柯克兰职业生涯历程)
柯克兰职业生涯的最后几年是艰难的。他在谢周三失去了一线队的位置,随后又在普雷斯顿北区担任替补,这让他“如释重负”,但也让他的职业专注度逐渐减弱。在家里,他变得与人疏远、性格焦躁。尽管他的妻子恳求他们谈谈他的情绪,但他含糊其辞,避而不谈。
他说:“我当时已经上瘾了。我无法扭转我的心态,无法扭转我的毒瘾。我的情况越来越糟。回到家我什么都不想做,不想社交,不想出门。最后,我不想踢足球了。”

(普雷斯顿北区时期的柯克兰)
柯克兰打算在普雷斯顿效力一年后就挂靴,但他想起了老球员们的忠告: “别急着退役,退役后的日子还很长。”他被说服加盟英甲升班马伯里队。他立刻意识到这是个错误——不是俱乐部的问题,而是他心态的问题。
一想到要在葡萄牙参加季前训练营,他就 “吓坏了”,感觉自己像个 “废人”。他回忆道:“第一天的训练并不顺利。第二天我吃了很多药片,很明显,这些药片让我发疯了。”
柯克兰回忆起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时不寒而栗:他心悸、呼吸急促、产生幻觉,几乎就像灵魂出窍一样,他发现自己躺在葡萄牙公寓楼的屋顶上,泪流满面,思考着不可想象的事情——他说:"够了。我打算跳下去。”
他说,在最后一刻,他 “感觉到了后退的力量”——家人的力量——他给妻子利昂娜打了电话,告诉她自己急需帮助。他说:“当时大约是凌晨两点半,她说:‘我们送你回家,找人帮你’。”
他先是对利昂娜,然后又对英格兰职业足球运动员协会(PFA)推荐的一位辅导员说,他坦白了一切:他的毒瘾有多深,他为掩盖毒瘾所做的努力有多大,他的无助感有多强烈。
他向伯里队当时的主教练大卫-弗利克罗夫特(David Flitcroft)坦白了一切,他说弗利克罗夫特 “非常出色”,俱乐部也同意解除他的合同。他开始“冷处理”这一切,不仅戒掉了曲马多,还退出了职业足球。他在一份简短的公开声明中说,为了家庭的利益,他需要离开足球运动一段时间。
有一段时间,他的做法奏效了。柯克兰达到了一个较好的境界,他不再怀念药物或比赛。但随后,毒瘾的戒断症状开始发作。“我开始怀念足球运动员的生活。我想念日常的生活,”柯克兰说,“我想过重新踢球,开始训练,但我的身体不愿意。我没有目标,我很痛苦,我很沮丧。我又开始吃药了。”
利昂娜发现了这些蛛丝马迹,于是进行了干预,求他去康复中心。他回来后神清气爽,有了新的目标感。他们一起去找他的医生,说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能给柯克兰开止痛药。针灸对他很有效果。
但随后又发生了新冠疫情、新的焦虑和毒瘾的缓慢复发。他没法做针灸来止疼,于是他发现自己又开始在网上订购止痛药。从海外寄来的包裹看起来平平无奇。他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药。他只知道这些药差点要了他的命。
他谈到了 “可怕的经历 ”和“不知道自己是谁”。出门在外,他会迷失方向,几乎不记得回家的路。
他又开始了同样的循环:心悸、昏厥、幻觉,再次无可救药地沉迷其中,对最亲近的人撒谎,直到恐惧的浪潮再次将他淹没,在妻子和女儿的恳求下,他又回到了戒毒所。
那是在 2022 年初。这一次,柯克兰带着不同的心态离开了康复中心,他知道自己的生命取决于能否战胜毒瘾。这是他对自己的承诺,但最重要的是对莉安娜和露西的承诺,他将她们的支持形容为 “不可思议”。

(历经三次反复终于戒掉毒瘾的柯克兰现况)
这一次,邮递员和送货司机被严令将任何可疑包裹直接交给他的妻子。除此之外,柯克兰还同意了一项安排,即他的妻子可以随时要求他接受药物测试。在我们采访期间,他身边放着一个测试工具。他很自豪能够直视别人的眼睛,坦陈自己已经戒毒两年半了。
他还为自己替利物浦基金会、球员工会和各种慈善机构所做的工作感到自豪——不仅仅是讲述自己的经历,他还参加了一系列竞走募捐活动。
这是他最近的嗜好,起初是受到前诺丁汉森林队和威尔士门将马克-克罗斯利的“行走的辉煌”慈善活动的启发,现在已经成了生活的一部分。也许是同为门将的缘故吧。
他说:“我肯定会觉得对运动上瘾。我今天已经在健身房锻炼了一个小时,但我计划晚些时候出去走 10 英里。利昂娜会说'休息一天吧',但我喜欢和狗一起在户外活动。如果不这样做,我一整天都会感觉很糟糕。所以这是一种瘾,没错,但这是一种健康的瘾。不像吃药。”
正是由于他的慈善工作,特别是提高人们对心理健康问题的认识,他最近获得了利物浦埃奇希尔大学的荣誉学位。
当时他被问及他的英格兰队队帽,他回答说,与惯例相反,他从未收到过。校方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了询问,英足总这才得知这位曾为英格兰队出场的球员竟然没有一顶真正的、实物的、戴在头上的帽子作为纪念,于是承诺会解决此事。
在本周对阵希腊的欧国联比赛之前,柯克兰将被授予属于他的、英格兰国家队第 1144 顶纪念帽,以表彰他在国家队的地位。他说,他为利物浦出场的意义远大于他为国家队出战的那场比赛,但他仍期待着温布利之行,期待着有机会与他在考文垂时候的队友、现任国家队临时主教练李-卡斯利见面。

(译者注:纪念帽长这样,马杜埃凯拿到的是第 1285 顶)
在许多退役球员开始发现自己陷入困境的时候,柯克兰却觉得自己已经重新找到了自我:他为利物浦基金会工作,在传奇比赛中受到安菲尔德球场的欢呼,获得了英格兰国家队的纪念帽——这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一个又一个问题正在被他用努力解决。
不过,到目前为止,最珍贵的还是与家人的重逢——看着女儿长大,彼此重逢。“她时不时地对他说:‘你真烦人。但我很高兴爸爸回来了。’”
原标题:
Chris Kirkland: ‘I was taking 2,500mg of Tramadol a day. I had it in my goalie bag on the pitch’

TA/Oliver Kay/2024-10-09
克里斯-柯克兰(Chris Kirkland)13 岁时,他的父亲埃迪(Eddie)走进一家投注站,询问他赌自己的儿子能为英格兰国家队出战的话,赔率是多少。
这已经成为博彩公司时常接到的询问之一,但在 1994 年,这并不寻常。他问了几个问题,比如这个男孩是否在职业俱乐部注册。答案是否定的。
博彩公司给出的赔率是1赔100,这促使埃迪下了 98.10 英镑的赌注。这是他和其他家庭成员所能凑到的最大赌注。
当时,柯克兰对他爹的这一奇思妙想一无所知。 他并不看好自己的机会,因为他在当地业余俱乐部巴威尔(Barwell)的 U14 足球队中一直难以获得一场比赛的机会。
三十年后,他在兰开夏郡的家中回忆道:“如果我和父亲一起去博彩公司,他们看到我,我肯定会给他开出比100倍更高的赔率。我当时非常臃肿。我的身材并不是最好的。”
当时,他在前一场比赛中被迫紧急充当门将这一陌生的角色,但表现得很出色。他说:“我的表现肯定没问题。我父亲一定看出了什么。我从将近 14 岁时第一次担任门将,到 18 岁时首次亮相英超联赛(代表考文垂)。这是一个火箭式升级的过程。”

(2000-01赛季,代表考文垂出战英超的柯克兰)
这是非同寻常的。2001 年 8 月,20 岁的他以 600 万英镑的身价加盟利物浦,成为英国最昂贵的门将。22 岁时,他首次获得英格兰国家队征召。当时唯一的意外是,一系列不合时宜的伤病让他不得不等到 25 岁才在与希腊的友谊赛中完成国家队首秀。直到那时,他父亲才终于得到了那笔意外之财。
但他的第一次代表国家队出场也是最后一次,而且由于至今仍不明确的原因,他从未获得过传统的国家队登场纪念帽。直到过去几个月,此事才引起英足总的注意,英足总连忙道歉,并承诺纠正此事。
因此,18 年后的周四,柯克兰将作为英足总的嘉宾,在温布利大球场再次见证英格兰队与希腊队的比赛。43 岁的他终于可以戴上自己的纪念帽了,但他更期待的是他十几岁的女儿露西。

(柯克兰在国家队的唯一一场比赛)
多年来,在柯克兰的成长过程中,他的足球生涯一直在被与折磨和创伤联系在一起——因为这正是足球给柯克兰带来的痛苦,他发现自己陷入了抑郁和止痛药成瘾的泥潭。
2016 年夏天,他在葡萄牙与伯里队一起参加季前训练营时,“服用了大量的药片”,这让他 “发疯”,险些丧命。就在那时,35 岁的他知道自己必须离开足球。是足球正在要了他的命。
直到现在,他才摆脱了毒瘾,重新振作起来。
今年 3 月,利物浦和阿贾克斯之间举行了一场传奇队比赛,为利物浦基金会筹集资金。
除了杰拉德、托雷斯和杜德克等球队传奇人物之外,柯克兰也被征召,这是他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比赛。
他在比赛中只出场了最后 11 分钟,是杜德克和桑德-韦斯特韦尔德之后的第三门将,但这已经足够了。
他说:“我根本不认为自己是利物浦的传奇人物。但当他们问我的时候,我想如果露西能看到我在安菲尔德踢球该有多好。虽然时间很短,但感觉非常棒。我真的没想到我上场时球迷们会这么欢迎我。”

(代表利物浦传奇队出场的柯克兰)
感觉就像回家一样。1988年,利物浦队以5比0大胜诺丁汉森林,这是柯克兰在利物浦的第一场比赛。
只是遗憾的是,他和其他人对自己的利物浦生涯寄予厚望,却从未真正起飞。
这是一笔奇怪的交易。
很少有人质疑利物浦承诺花费高达 600 万英镑购买一名年轻门将的逻辑,因为这名年轻门将在考文垂取代瑞典门将马格努斯-赫德曼后表现出色,被广泛认为是英格兰国门的潜在接班人。
但奇怪的是,利物浦在同一天从费耶诺德签下了波兰国门杜德克。在他下笔之前,接班的计划就已经很明显了——28岁的杜德克负责中短期,20岁的柯克兰负责长期。但在与“令人敬畏”的杜德克进行了一次训练后,柯克兰不知道自己还需要等待多久。

(杜德克和柯克兰是同一天官宣的)
在杜德克状态严重下滑后,柯克兰在默西塞德郡的第二个赛季获得了出场机会,但令人鼓舞的表现却因他在足总杯比赛中与水晶宫前锋德勒-阿德博拉相撞导致右膝后十字韧带断裂而戛然而止。
伤病成了他生存的祸根:手指骨折;在训练中阻挡哈里-科威尔(Harry Kewell)的凶猛射门时手腕骨折;困扰他多年的背伤,最初是在另一次训练中发作,这次是因为蛙跳;2005 年 10 月租借到西布罗姆维奇时,他在与博尔顿流浪者前锋凯文-戴维斯(Kevin Davies)的冲撞中肾脏撕裂。
他说:“我并不是那种肌肉经常受伤的人。那是一连串的意外受伤。”
这些伤病似乎总是在最糟糕的时候发生:他第一次担任利物浦门将出战了 14 场比赛,第二次出战了 11 场比赛,第三次出战了 14 场比赛。2004 年 12 月,在史蒂文-杰拉德(Steven Gerrard)的激励下,利物浦在安菲尔德战胜奥林匹亚科斯,他还在那场著名比赛的板凳席上,但五个月后,当利物浦队在伊斯坦布尔战胜 AC 米兰时,他已无缘欧冠赛场。
后备门将斯科特-卡森(Scott Carson)在赛后为他颁发了冠军奖牌,并指出柯克兰在小组赛中首发出战了四场比赛。但柯克兰拒绝了这块奖牌,他觉得自己没有参与其中。因为背部手术,他无法在贝尼特斯手下看到自己的未来。
离开利物浦后,柯克兰在维冈竞技担任了四个赛季的首发门将,基本上没有受到伤病的困扰,帮助球队留在了英超联赛,并在 2008 年赢得了俱乐部的年度最佳球员奖。他毫不犹豫地将那段时光称为 “我职业生涯中最美好的时光”。

(维冈竞技时期的柯克兰)
2012 年夏天,当柯克兰签约谢周三时,俱乐部坚持在他的合同中加入一项条款,规定如果他因背伤缺席达到一定场次的比赛,俱乐部可以终止与他的合同。
柯克兰确信他的背伤问题已成为过去,但在谢周三英冠联赛揭幕战的前两天,他的背部突然痉挛,这让他陷入了焦虑和恐慌之中,担心所有的老伤病和老毛病都会卷土重来。
过去,当他的背部问题最严重时,医生曾给他开过止痛片曲马多(Tramadol,一种具有成瘾性的止痛药物,被滥用规模最大的精神药品之一)。他感到绝望,于是自作主张,自行用药,宣布自己康复了,并在与德比郡的比赛中再次感觉良好。
但很快,他就发现自己吃药不仅仅是为了治背痛。他这样做是为了缓解从来到谢周三那一刻起就感到的焦虑。
他说:“这是一家伟大的俱乐部——大俱乐部,伟大的球迷——但我的问题是远离家乡。我错过了一切:接女儿放学、看她的校园剧、下午遛狗。我在利物浦和维冈时的日常工作都不复存在了。我还要开车去谢菲尔德——单程只有70英里,但通勤时间太长了,要穿过蛇形山口,高峰时段还要堵在曼彻斯特的路上。”
他说:“我开始在早上 5:45 出发,比其他人早几个小时到达训练场。我真的很焦虑,所以我开始服用更多的药物来缓解焦虑。我的情况越来越糟。曲马多每天最多只能服用 400 毫克。我每天服用 2500 毫克。我把它们装在守门员包里带到球场上。不是因为疼痛,而是因为我上瘾了。我每天醒来第一件事就是吃药,晚上最后一件事也是吃药。”
俱乐部里有人知道他在服用吗?或者他的医生?“不知道,”他说,“我是在网上订购的。没有人知道,甚至利昂娜(柯克兰的妻子)也不知道。”
九个月前,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ADA)将曲马多列入了禁药名单,这意味着如果运动员在赛内检测中对该药物呈阳性反应,将面临长期禁赛的前景。
在过去几年中,有球员私下联系柯克兰,请求帮助他们戒掉止痛药。他说:“我不是说每个球员都这样,但药物成瘾的运动员比你想象的要多。现在止痛药已被列入禁药名单,但如果有人被发现服用止痛药,我也不会感到惊讶。
“它们不会提高成绩。它们不会让你变成超人,也不会让你扑出每一球。它们很危险。这就是问题所在。我曾晕倒、心悸、产生幻觉,病得很重。它们会杀了你,而且它们差点就杀了我。”

(译者注:德转的柯克兰职业生涯历程)
柯克兰职业生涯的最后几年是艰难的。他在谢周三失去了一线队的位置,随后又在普雷斯顿北区担任替补,这让他“如释重负”,但也让他的职业专注度逐渐减弱。在家里,他变得与人疏远、性格焦躁。尽管他的妻子恳求他们谈谈他的情绪,但他含糊其辞,避而不谈。
他说:“我当时已经上瘾了。我无法扭转我的心态,无法扭转我的毒瘾。我的情况越来越糟。回到家我什么都不想做,不想社交,不想出门。最后,我不想踢足球了。”

(普雷斯顿北区时期的柯克兰)
柯克兰打算在普雷斯顿效力一年后就挂靴,但他想起了老球员们的忠告: “别急着退役,退役后的日子还很长。”他被说服加盟英甲升班马伯里队。他立刻意识到这是个错误——不是俱乐部的问题,而是他心态的问题。
一想到要在葡萄牙参加季前训练营,他就 “吓坏了”,感觉自己像个 “废人”。他回忆道:“第一天的训练并不顺利。第二天我吃了很多药片,很明显,这些药片让我发疯了。”
柯克兰回忆起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时不寒而栗:他心悸、呼吸急促、产生幻觉,几乎就像灵魂出窍一样,他发现自己躺在葡萄牙公寓楼的屋顶上,泪流满面,思考着不可想象的事情——他说:"够了。我打算跳下去。”
他说,在最后一刻,他 “感觉到了后退的力量”——家人的力量——他给妻子利昂娜打了电话,告诉她自己急需帮助。他说:“当时大约是凌晨两点半,她说:‘我们送你回家,找人帮你’。”
他先是对利昂娜,然后又对英格兰职业足球运动员协会(PFA)推荐的一位辅导员说,他坦白了一切:他的毒瘾有多深,他为掩盖毒瘾所做的努力有多大,他的无助感有多强烈。
他向伯里队当时的主教练大卫-弗利克罗夫特(David Flitcroft)坦白了一切,他说弗利克罗夫特 “非常出色”,俱乐部也同意解除他的合同。他开始“冷处理”这一切,不仅戒掉了曲马多,还退出了职业足球。他在一份简短的公开声明中说,为了家庭的利益,他需要离开足球运动一段时间。
有一段时间,他的做法奏效了。柯克兰达到了一个较好的境界,他不再怀念药物或比赛。但随后,毒瘾的戒断症状开始发作。“我开始怀念足球运动员的生活。我想念日常的生活,”柯克兰说,“我想过重新踢球,开始训练,但我的身体不愿意。我没有目标,我很痛苦,我很沮丧。我又开始吃药了。”
利昂娜发现了这些蛛丝马迹,于是进行了干预,求他去康复中心。他回来后神清气爽,有了新的目标感。他们一起去找他的医生,说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能给柯克兰开止痛药。针灸对他很有效果。
但随后又发生了新冠疫情、新的焦虑和毒瘾的缓慢复发。他没法做针灸来止疼,于是他发现自己又开始在网上订购止痛药。从海外寄来的包裹看起来平平无奇。他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药。他只知道这些药差点要了他的命。
他谈到了 “可怕的经历 ”和“不知道自己是谁”。出门在外,他会迷失方向,几乎不记得回家的路。
他又开始了同样的循环:心悸、昏厥、幻觉,再次无可救药地沉迷其中,对最亲近的人撒谎,直到恐惧的浪潮再次将他淹没,在妻子和女儿的恳求下,他又回到了戒毒所。
那是在 2022 年初。这一次,柯克兰带着不同的心态离开了康复中心,他知道自己的生命取决于能否战胜毒瘾。这是他对自己的承诺,但最重要的是对莉安娜和露西的承诺,他将她们的支持形容为 “不可思议”。

(历经三次反复终于戒掉毒瘾的柯克兰现况)
这一次,邮递员和送货司机被严令将任何可疑包裹直接交给他的妻子。除此之外,柯克兰还同意了一项安排,即他的妻子可以随时要求他接受药物测试。在我们采访期间,他身边放着一个测试工具。他很自豪能够直视别人的眼睛,坦陈自己已经戒毒两年半了。
他还为自己替利物浦基金会、球员工会和各种慈善机构所做的工作感到自豪——不仅仅是讲述自己的经历,他还参加了一系列竞走募捐活动。
这是他最近的嗜好,起初是受到前诺丁汉森林队和威尔士门将马克-克罗斯利的“行走的辉煌”慈善活动的启发,现在已经成了生活的一部分。也许是同为门将的缘故吧。
他说:“我肯定会觉得对运动上瘾。我今天已经在健身房锻炼了一个小时,但我计划晚些时候出去走 10 英里。利昂娜会说'休息一天吧',但我喜欢和狗一起在户外活动。如果不这样做,我一整天都会感觉很糟糕。所以这是一种瘾,没错,但这是一种健康的瘾。不像吃药。”
正是由于他的慈善工作,特别是提高人们对心理健康问题的认识,他最近获得了利物浦埃奇希尔大学的荣誉学位。
当时他被问及他的英格兰队队帽,他回答说,与惯例相反,他从未收到过。校方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了询问,英足总这才得知这位曾为英格兰队出场的球员竟然没有一顶真正的、实物的、戴在头上的帽子作为纪念,于是承诺会解决此事。
在本周对阵希腊的欧国联比赛之前,柯克兰将被授予属于他的、英格兰国家队第 1144 顶纪念帽,以表彰他在国家队的地位。他说,他为利物浦出场的意义远大于他为国家队出战的那场比赛,但他仍期待着温布利之行,期待着有机会与他在考文垂时候的队友、现任国家队临时主教练李-卡斯利见面。

(译者注:纪念帽长这样,马杜埃凯拿到的是第 1285 顶)
在许多退役球员开始发现自己陷入困境的时候,柯克兰却觉得自己已经重新找到了自我:他为利物浦基金会工作,在传奇比赛中受到安菲尔德球场的欢呼,获得了英格兰国家队的纪念帽——这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一个又一个问题正在被他用努力解决。
不过,到目前为止,最珍贵的还是与家人的重逢——看着女儿长大,彼此重逢。“她时不时地对他说:‘你真烦人。但我很高兴爸爸回来了。’”
原标题:
Chris Kirkland: ‘I was taking 2,500mg of Tramadol a day. I had it in my goalie bag on the pitch’